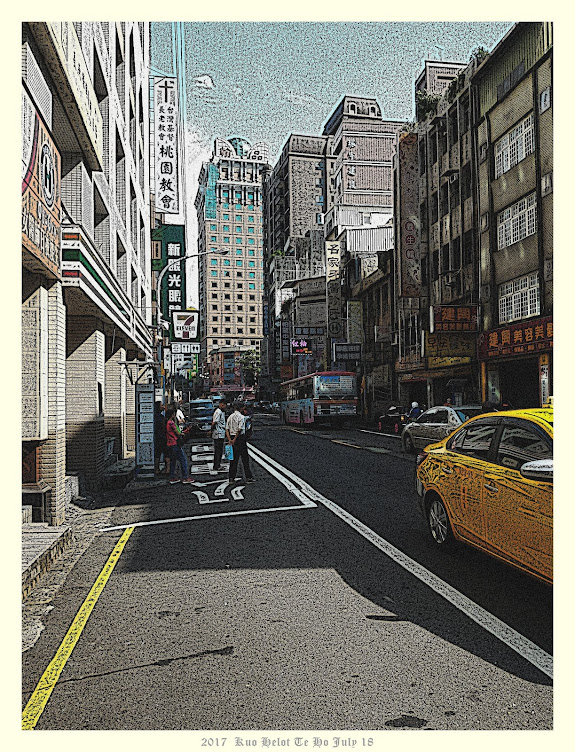謝謝妳的八○年代回憶,我很久沒去想過去的事,因為常常想了半天,總是拼不出來完整的記憶。過去的叫做歷史,未來的稱為科學,那現在呢?我實在想不出一個詞來形容現在,會不會根本沒有所謂的現在呢?我們回憶過去的種種,我們憧憬未來的可能,我們無所謂現在。好吧!我承認那個對著油畫傻笑的高中生,已經沒有歷史,也不科學,二○○七年,現在,重新遇見妳。
觀察敏銳,依然沒變,是的,現在我很少喝酒,並不是什麼養生,而是一個人喝酒沒什麼意思。咖啡不是什麼陰影,年少的思維總是帶著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青澀,骨子裡卻少了生活的真實面貌。妳喝過耶加雪菲這種咖啡嗎?像極了三天沒有清洗的襪子,又像是潮濕徘徊不去的閣樓,真實極了!想喝酒,改天一起喝個痛快吧!不過林旺已經離開很久了,令妳讚嘆的陽具也跟著離開。某個程度而言,我現在的生活並沒有少年時的痛苦想像,一個人越年輕就越無法認識痛苦,真正的痛苦無法言說,也沒有可以依附的具體事件,沒有人知道痛苦究竟是什麼?
但是快樂卻是件廉價的過季衣裳,惹人會心,一笑。最近我常常想到《王子半月刊》這本小時候讀的雜誌,這本雜誌每期都會連載校園愛情故事,很單純的愛情,沒有肉體的接觸,沒有瓊瑤式的海灘相擁,只有眼神的交纏,只有內心的想望,只有一期又一期的期待。說實話,故事情節都忘光了,但是腦海裡似乎永遠有個位置無法抹去,一種陽光燦爛的濃濃氣味。好幾次逛舊書攤,都看不到這本雜誌,真想知道作者是誰?
老實說,我一點都不懷念八○年代的台北,當年忠孝東路滿滿的沙龍,只是反映當時莫名其妙的經濟奇蹟,沙龍的存在證明Helot的說法,藝術只是一種裝飾,裝飾經濟奇蹟的牆壁,填補有錢人的虛榮。妳知道嗎?好像贖罪券一樣,一幅幅數十萬的油畫宣告著文明的品味。如今沙龍不再,只代表我們認清了自己,八○年代牆上掛的油畫實際上是一面鏡子,只是這鏡子看不到真實的面貌,有歐洲人、日本人、美國人還有非洲人,就是看不到自己。歐!忘了一件事,看不見的還有俄國人與東歐人,因為他們是敵人,想看俄國人的話,就去明星喝杯咖啡吧!
我無意打擊妳對過去的美學經驗,我只是坦率的表達我的看法,這樣吧!改天一起去北美館晃晃,搞不好我們會看見過去的我們,或者去師大路吃碗三色豆花,喝杯泡沫綠茶,也挺不錯的!
願妳一切順利
Markus